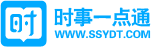时事评论背景:
官员的秘书问题近日被屡屡媒体被关注到。4月24日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,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,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,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,“不能认为‘机关牌子大、领导靠山硬’而有所依仗、有恃无恐,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”。据报道,去年来云南、广西、河北省平山县都曾下发通知,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。
时事评论观点:如何看待“ “秘书病””问题
当媒体在谈论“秘书病”时,它们究竟在谈论什么?显然的是,这重点指向的其实是两个重要的问题。一是部分官员秘书的过多现象,1980年,中办发布《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》明确,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。但放眼现实,为县处级领导配备专职秘书者都随处可见;二是秘书腐败现象的接踵出现。近年来,不仅官员与秘书连续落马的新闻时常见诸报道,甚至秘书成为领导“贪腐掮客”的也不鲜见。
客观地评价,就媒体所指出的这两种“秘书病”而言,后者的纠偏难度无疑要远甚于前者。因为针对秘书数量过于泛滥的现象,进行强制性的规定,或者进行秘书制度的相应改革,它的治理效果应该可以被想象。但具体到“秘书腐败”的问题上,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。部分官员的秘书为什么会成为那个轻易腐败的群体?自然是因为他们分享或延伸了领导手中的部分权力,进而利用这部分权力寻租。由此出现了“二号首长”“XX第一秘”等匪夷所思的怪现状。
以上是并不难厘清的逻辑:其实所谓的“司机腐败”、领导家人腐败和秘书腐败有着共同的根源。那就是一些官员手中就掌握着不受约束的权力,或是局部的行政运行没有被严格限制在法治范围内。没有被关进笼子的权力,一旦邂逅到本身就存在着弹性空间的行政生态,那么“与领导亲近的人“,自然更容易获得某种寻租的机会。此时倘若其中的领导人自身亦存在贪腐的事实,那么秘书成为“贪腐掮客”就会顺理成章。并且,因为特殊的身份,秘书会更快地推动贪腐官员的堕落化进程,且让此种腐败具有特别的隐蔽性。
“秘书病”不是今日才出现,“秘书腐败”遵循的也是“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边界的地方为止”的定律。治理“秘书病”其实无需新认识,约束好权力、依法依规行政即可。这样的判断,今天还可以再说一遍。